对话白志东先生
陈松蹊 概率统计学会 2023-11-30 17:48 发表于江苏
本文由陈松蹊在2018年11月14日于白志东教授在东北师大办公室进行了4个半小时的访谈整理而成。
白志东1943年生于河北省乐亭县。196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1982年获博士学位,是新中国首批18个博士之一。1984年9月起先后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和宾州州立大学统计系担任研究员,美国天普大学统计系担任副教授,台湾中山大学应用数学系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概率统计系担任教授。2002年5月加盟东北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担任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大维随机矩阵和数理统计理论方面研究,目前已发表学术论文近300篇,出版学术专著6部,SCI引用4000余次。现任学术期刊《Random Matrix: Theory and Applications》创刊主编、《Journal of Statistical Planning and Inference》、《Statistical Paper》的Associate Editor,曾任《Journal of Multivariate Analysis》、《Statistica Sinica》、《Sankya》等学术期刊的Associate Editor。他是 IMS (the Institute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的Fellow,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独立完成人),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独立完成人)。自2016年至今,连续7年上榜爱思维尔“中国高被引学者”,连续入选世界顶级2%学者等。

白老师和夫人与陈松蹊,郑术蓉合影。
摄于2023年11月25日
访谈
陈老师:白老师,非常高兴来采访您。再过不到两周就是您的75岁生日,先预祝您生日快乐!
白老师:谢谢。
陈老师:您是1943年出生的。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您父母的情况,还有当时中国的情况以及您出生地的情况?
白老师:从我出生的年代可以看出来,当时中国正处在抗战时期。我出生在1943年,阴历是10月29号,阳历是11月26号。我出生的地方比较偏僻,靠近渤海向北的乐亭县。抗战以前,我们那个地方处于东北和华北之间,要么直系来,要么奉系来,国民党中央没有统治过那个地方。抗战开始后,日本鬼子先来了,后来八路军来了。所以我们那里的老百姓是见到共产党比国民党要早,因为日本鬼子先进来的,然后是共产党,八路军进来了。因为当时这个情况,我出生的时候,当地老百姓都是支持抗日的。我的亲生父母家庭条件稍微好一点,但是也不是很富裕,达不到地主那种地步。我亲生父亲小的时候在东北沈阳(当时叫奉天)当过店员。后来东北一沦陷他就回老家了。共产党来了以后,他跟着共产党抗日。我的生父和我的养父都是村里面的干部。因为我生父原来在东北当过店员,会写、会算、会记账,农村能找到一个会认字的人都很少,所以他相当于知识分子了。当时共产党成立村政府,我亲生父亲在村政府一开始管钱粮。“钱”就是出纳,“粮”就是保管员,农民交了公粮,都是村政府管着,八路军进村后要吃要用都是从他们那边出。我的养父当时负责抗日勤务工作,八路军来了以后的吃、住和通讯都是我养父做这个事情。我的生父和养父关系比较好。后来村上的会计叛变了,被日本鬼子收买了。会计没有人做了,所以让我生父又管钱粮又当会计。后来日本鬼子投降以后,国民党来了。国民党来了以后我们老百姓叫“闹中央军”,大概是1946年的时候。
陈老师:为什么叫“闹”?
白老师:从这个闹字可以看出来老百姓对中央军是不欢迎的。中央军来了,他们跟我生父要共产党的账,家里面的人商量后说这个账不能给。我生父想,虽然不知道将来天下是谁的,万一哪一天共产党回来跟我要这个账,我这个账给了国民党了,我不就是叛徒吗?他不敢把这个账给国民党,国民党又逼着他交,他就把账簿埋到坟地里面,自己又跑沈阳去了。他跑以后,我们家的地就没有人管了。当时我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妹妹,妹妹刚出生。1945年,家里面的地实际上没有人管了,到后来家里面雇了一个长工。本来1947年土改的时候我们家定的是中农,后来就是因为雇了这个长工,爷爷和村干部吵架,给改成了富农。当时,我家里面有16亩地,我一个大伯死了以后留下19亩地,还有一个我三叔(我爷爷弟弟的儿子)他家里面有29亩地。我三叔参军了,当了解放军,后来牺牲在朝鲜,所以他家里面的地都是我父亲管着,一共50-60亩地。当时我爷爷身体还健康,我哥哥也能多少干一点活,原来我生父在家的时候,就没有必要雇长工。国民党向他讨账,他不得不跑掉了。我生父跑掉以后,因为养父家里面什么也没有,没有房没有地,所以家里面的事情经常由我的养父来帮忙。当时我下面有了一个妹妹,家里面没有人管我。我当时住在一个大笸箩里面,你知道笸箩吗?
陈老师:我知道,就是草编的。
白老师:是柳条编的。小时候我被放在笸箩里面,没有人管我。反正窝窝头什么的丢到里面,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没人管我。
陈老师:您的母亲呢?
白老师:我母亲生了一个妹妹,要管我妹妹。我的哥哥比我大三岁。我那个时候还不会走,只能放在笸箩里面,爬来爬去。我养父看我可怜,就抱回家去,由我养母带着,她没有儿女,很喜欢小孩。晚上抱回来我就不干了,抱回来没有人管我,抱去高高兴兴,抱回来我就又哭又闹。
陈老师:待遇不好,没人管您。
白老师:没有办法,就这个样子我就在养父那里生活下来了。生父和养父都是好朋友。
陈老师:白是养父的姓。
白老师:对。
陈老师:您是哪一年进的小学?
白老师:应该是1951年春天,1957年毕业。
陈老师:河北乐亭那个小学是什么样子?
白老师:小学是由过去成立的抗日学校扩编的。当时是初小(由一至四年级组成的小学),解放后才成立完小(由一年级到六年级组成的小学)。小学也分初级和高级——初小和高小。我们那个学校有五年级和六年级所以是完小,我是我们这个学校的第二届高小毕业生。
陈老师:完小很普遍吗?
白老师:我们那个乡里只有我们一个完小,其他的都是初小。他们念到一二三四年级,然后并到我们学校。我们学校过去是一个关帝庙。解放以后需要一个地方成立学校,当时政府没有钱,盖房也盖不起,就利用了现成的大庙。关帝庙大厅里面,钉四块板子当作黑板。四个年级在同一个大厅上课,这边两个那边两个,一个老师一个黑板,这个一年级,那个二年级,三、四年级都在一个课堂上课。学生有能力可以同时上四门课,想听谁的听谁的。
陈老师:可以同时上四门课?您是不是在这个班上听其他班的课?
白老师:别人的课也听一听。学校也没有什么正规老师,大多数老师都是复员军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都是要求学文化课,白天打仗,晚上念书。他们能认识字,他们可以给学生上课了。我们就是那样的一个学校,课桌就是一块大板子两头钉在木桩上,每个学生分一块地方来学习。板凳是从家里带的。
陈老师:要走多远?
白老师:大概一里多一点,我们走过一个村庄就到学校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上学的环境是很艰苦的,但是当时并不觉得艰苦,反正有地方上学就很好了,大家都是那样。
陈老师:您是1957年上的初中?
白老师:1957年考的初中,我是第二届。
陈老师:那个初中条件比小学好一点?
白老师:比小学房子新,桌子是一个人一个桌。但是比起高中差的很远。小学没有桌子,钉的板子,相比较而言这个初中好多了。
陈老师:那个时候您对数学表现出来很高的兴趣?
白老师:我们学校刚毕业的学生分到我们那当老师,我记得叫张景林,教我们平面几何的,他搞了一次数学竞赛。当时我们走读回家,离家还有十里地,所以考试的时候很多学生问老师答不完怎么办?我说你们答不完?我可是要回家了。后来我得了第一名。初三的时候我们学校两个班搞了一次数学竞赛我得第一名。反正我从小学开始觉得数学好像没有难过。你知道那个时候农村打算盘吗?从二归到九归我都会打,但我不知道归就是除法。后来到四年级的时候一个老师要我帮他算成绩,算每个学生的平均成绩,他告诉我几门成绩加起来算一个平均数,我说我不会打除法。他说你不是会打三归吗?三门课加起来除三。我说三归会。从那以后才知道归就是除法。
陈老师:您1960年上高中,是到另外一个地方?
白老师:在乐亭县城。我考的高中是二中,实验性的两年制的。当时是三年困难时期,60年考上高中时还挺好的,放寒假回去以后就不行了。再回去以后是1961年春天了。
陈老师:由于这三年的自然灾害,高中推迟了一年?
白老师:是的,90%的学生都回农村去种地了。我们二中四个班留了17个学生并到一中去了,这个二中都下马了。我们二中的四个班,两百多个学生,就剩下17个人并到一中去了。
陈老师:那么入高中以后,一开始上什么课?
白老师:1960年的时候还没有困难,1961年才困难。我高中相当于念了三次。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哥哥给我一套高中的课本,他到内蒙古念医专,他整个高中的课都学了,然后他把整套高中课本给我。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把高中课本自学了一遍,上高中就不紧张了,就不难了。上高中以后,二中是个两年制学校,一年把三年课教完,还有一年准备复习高考。念了一年,二中下马了,并到一中去重新学。因为一中是三年制,我的高中课相当于学了三遍。
陈老师:您说一下1961年的情况,当时的饥荒比较严重的,对你们上学有没有影响?
白老师:有影响。我小时候在农村,没有睡午觉的习惯,不知道睡午觉是什么?我小时候睡觉很少的,都是天不亮三四点爬起来跑出去玩儿了,大人也不太管,他们要睡觉。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控制粮食,说一天供应四两粮。然后节约一两做战备,一天只吃三两粮。这时就不能随便玩了,玩会把吃的东西都消耗光了,怕到时候营养不够。所以老师要求学生必须睡觉够一圈---从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当老师很辛苦的,搬个凳子坐到学生宿舍里面,直到所有的学生都睡着了,老师才能走。养成睡觉的习惯都是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硬被老师训练出来的。
陈老师:1962年情况好一点吗?
白老师:1963年好一点,1962年还不太行。
陈老师:您是1963年上的大学,当时考大学,为什么考中国科大,因为当时它是一个比较新的学校?
白老师:说起考大学,是一件很好玩儿的事儿。我们中学,从校长到教导主任,都是特别负责任的领导。每个学生学习怎么样,校长和书记他们都了如指掌。任课老师更是这样,对学生的情况掌握非常透彻。当时也强调升学率。学校掌握每个学生的能力,能够考到哪个学校去。学校掌握的情况,几乎没有什么错误的。到报考的时候,每个学生报考的第一志愿比能力稍微高一点,第二志愿一定比你这个能考的能力稍微低一点的学校。就是说你第一志愿可能会比期望的好一点,考不上的话第二志愿基本保证一定录取。当时我们是每个学生可以报三十个志愿。如果第一个没考好,保证你第二个一定会录取。如果那些都考不上的,学校就不太管了,放羊了,随便你怎么报。我们学校是这么一个学校。我的上一个年级,有一个学生叫邢少文,他成绩好,家庭出身也好,学校让他准备保送军校。军校当时是超倍保送的,如果准备招一百个人,就要求中学推荐二百个人,保证两个人取一个。他各个方面条件都好。因为城市里保送军校不给好学生的。而农村的考上军校也是一个升学率,也算是考上大学了。所以农村尽量把好学生往军校报。我们学校里面,从有高中毕业生开始,报军校没有考不取的。所以这些学生报考志愿的时候学校就不管了,反正他是军校录取了,军校先录取,考不上了再由普通学校录取。因此他的报考志愿没有人管了。结果不知哪个环节,保送军校出了问题,所以他没有被军校录取。由于他报了中国科技大学。然后就被录取了。考取了以后我们这个年级就来了一个任务,科大至少报一个学生进去。因为当时的录取情况,和你们后来录取情况不一样,你们是文化革命以后。
陈老师:对,我是1979年。所以科大就对你的高中产生兴趣了。
白老师:当时录取规定是这样,我们成绩按照五分一段算的。你这个学校85-90分一段,你可以同一段里挑任何一个人,你可以要85,86的,不要89的。同一段可以要任何一个人。但如果不是同一段,那么是违规的。如果这个大学每年招这个中学,这个学校对这个中学产生一个好感,这个学校的学生不错,于是可能宁愿要86的不要89的,因为他的学校好。所以说我们学校考了一个科大,必须每年都给他送一个,让科大对我们的中学产生好感。当时我们学校升学率是这样的,大概1956年招第一批学生,1959年的第一届毕业生,全部都录取了。因为农村学生出身好,1959年讲成分是比较厉害的,大约100%升了大学。到1960年以后,开始不太讲家庭出身了,好像1960年还讲的。1960年考上大学的,大约是60%、70%升学率。农村能考取3%就差不多了,因为当时全国的升学率也就是3%左右,那么60%~70%相当不简单了。
陈老师:有考上其他大学的吗?
白老师:我们学校当时考北大的从来没有过,所以学校不鼓励考北大。考清华的每年至少有三、四个。当时,我们报清华的已经有十五个人了,最后取了五个。报考科大的只有半个。我们学校有一个叫何树宾的,他说我学习比他好,我报他就报,我不报他也不报。我就成为一个关键人物,我不报就没有人报科大了。这意味着去年白考了一个,今年断弦了。于是,学校的校长,书记,教导主任,三个人车轮战和我谈话,动员我报科大。我吃了早餐,校长就过来了,说吃完饭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陈老师:您当时想去哪个学校?
白老师:我是想报清华的。因为和我最好的老师,是教我们代数的苗新亭老师,他一辈子考了三次清华没有考取。解放前都是学校录取,这个学校没考上就没考上了,不同时录取,他一辈子考三次清华没有上去,他特别希望报清华。最后那个老师是考到北京政法学院学法律了,后来到我们学校教代数。那个老师教的非常好,整个唐山地区都是很有名的老师。他每年都去参加改高考卷子。唐山一中校长和他说“你调到我们学校来吧,我们工资给你涨两级,全家解决城市户口”。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你这个条件非常诱人,但是我不能来。问他为什么不能来,他说我来了对不起我们老校长。
陈老师:是的。
白老师:那么就是说一家人都是农村户口,我这个校长对我好,我只有给他卖命。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那个校长对学校的老师怎么样。再给你讲一下他跟我之间的故事。校长不是动员我考科大吗?于是校长讲大道理,你不能从个人兴趣出发,要为党争光,为学校争光。校长谈完书记又来了。我是农村学生不会说什么,你们说什么我听什么,我不说话。苗老师动员我去清华,他说你听我的,你考清华没有错。他说我知道你这孩子不听话,过去不听话算了,这次要听我一次。所有任课老师都动员我考清华,只有这三个人不同意。别的学生都去复习功课了,那时也没课了。高三都是复习功课,化学课是化学老师来辅导,几何课是几何老师来辅导。就这样,每天所有学生在课堂复习功课,而我一个礼拜就和这三个人车轮战,和我谈话。最后没有办法,老是这样不答应也不行,看书也看不成了,最后说报科大就报科大吧。
陈老师:科大也是非常好的学校。
白老师:科大也是非常好,当时对其他的专业不太了解,那就报数学了,我数学好一点。
陈老师:当时科大是一个新的学校,当时在北京吧?
白老师:对,是在北京,科大是1958年成立的。
陈老师:所以您是1963入学。
白老师:是第六届毕业生。

华罗庚教授与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师生员工合影,从左至右,第二排:华罗庚(第31),王元(第33),殷涌泉(第37);第三排:方兆本(第31),韦来生(第33),白志东(第48),缪柏其(第50)。摄于1981年。
陈老师:您到科大以后,适应它的生活吗?你对教学和生活是不是比较满意?
白老师:一开始比较难,因为我是一个农村学生,听南方的普通话听不懂。
陈老师:老师很多是南方人?
白老师:很多都是南方人,龚昇、许以超等基本都是江浙一带的人。
陈老师: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
白老师:对,都是非常好的老师。但是第一年的时候我基本跟不上,到了后面可以听懂他们的话就好了,后来就适应了。从大学二年级以后,教我课的老师知道我学习好,之前教我的老师不知道我学习好,因为当时我听不懂老师的话。后面我发现听不懂也有好处,你必须看书,自学能力就是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非自己看书不可。龚昇给我们讲课怎么讲的?他第一堂给我们讲课,我们用的书都是华罗庚编写的,华罗庚说把数学分析等整个的数学内容都放在一起叫作《高等数学引论》。上第一堂课,说大家打开第23页,说第1-22页华副校长写的很清楚,你们大家自己回去读一读就行了。他说第23页这有一个“不难看出”,这个对华副校长不难看出,对你们就不见得一眼能看明白,这一点证明我给大家补充一下。然后他就讲了20分钟。然后他说下面写的很清楚,很精彩,我给大家读一读,大家共同欣赏。然后他的南方口音一读我就听不懂。讲数学就是不用南方口音,念出来也一般听不懂。
陈老师:这是第一堂课。
白老师:对,前面22页不讲了,自己回去看,后面一个不难看出,然后念了很大的一段,然后说不难证明,其实让你们证明还是比较难的,一次课两节课连在一起,中间不休息。
陈老师:当时教学有关龙、华龙两个团队?
白老师:实际上三条龙,还有一个吴文俊。因为吴文俊不教基础课,吴文俊的年级是由华龙的一批人马帮助他教基础课的。当时三个人,华龙和关肇直还有吴文俊。三个年级,1958年是华龙的,1959年是关龙的,1960年是吴文俊的,然后再三个人轮流上。我们第六届的应该是吴文俊的,但是基础课是华龙帮他教的。
陈老师:您很多都是自学的是吧?而且龚昇老师也不细讲,主要让你自己去看。
白老师:是的,我基本都是自学的。对,因为他补充了的你记下来了,你看书不懂了再看他讲的才能看明白,直接听他讲你也听不懂。他讲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华罗庚的书上写着“不难证明”或“不难看出”的部分,他给予了补充。课前预习了一遍之后再听他的课,就容易懂了。
陈老师:当时您读本科的时候,最后有没有选专业?
白老师:我们前面两年没分专业,到了1965年开始分专业了,当时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统计,一个运筹。是要我们自己报名的,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运筹学,因为运筹学中优化的概念是很清晰的,比如线性规划或者线性函数怎么找最优解一类的问题。当时我报的运筹,但是学校不同意,说你必须分到统计专业里面。
陈老师:当时是概率统计还是就是统计?
白老师:当时就是统计专业和运筹专业。学校说运筹里面没有太多的理论的东西,理论的东西还是在统计里面的。所以系里基本把学习好的都放到统计专业里面。这样,学校就硬把我分到统计里面了。
陈老师:当时统计老师是哪些老师?
白老师:当时的统计老师讲的都是应用统计,老师有杨纪珂。杨纪珂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后来到安徽省做了副省长。当年国民党把他公费派到美国留学,那时候他是学生物的。到了美国以后,他自己开了一个理发店赚留学生的钱,赚钱以后他又开了一个餐馆,再赚了钱他又买了一块地自己开农场,他在美国拿到一个Master,Ph.D 没念。这时国民党政府发现他在外面打工,开饭馆什么的就不给他奖学金了,他就念不下去了。后来学统计是因为他搞农场需要用到统计,因为知识分子不像农民光是种地收获就行了,他要研究怎么把这个地种好,他有很多这方面的科学研究。而且当时他夫人是学统计的,就教他统计,怎么给农田做实验这些东西。解放以后,由于国民党在他留学期间把奖学金给他断了,他就不愿意去台湾,他就回了大陆。回大陆以后,他给我们上统计的课。统计都用的坐标纸,都是他从美国带来的,中国当时没有坐标纸,还有对数纸,正态纸,双对数纸等等。现在我们做QQ-plot,把坐标点进去就是一条直线了,还可以做变换。他(杨纪珂)是已经把那个变换好了的,直接按照坐标往里填,是一条直线的就是正态的,不是一条直线的就不是正态的。
陈老师:看来杨老师也是一个很奇特的人,给你讲应用统计。
白老师:讲应用课讲的很好,后来理论课就是陈希孺讲了。
陈老师:您对统计很喜欢吧?
白老师:学这个的,不喜欢不行,都已经是自己的专业了。
陈老师:这是1965年分专业,到1966年文革开始了。我记得1966年5月份文化大革命开始热闹起来。那秋天的课还在上吗?
白老师:秋天就不上了。本来7月份高考,高考就停了。高考停了也是那些高考生造反的,说高考是资产阶级招生制度什么的。
陈老师:所以1966年停课,停了多长时间?
白老师:1967年搞过一回复课。
陈老师:文革当中您自己受到了冲击吗?
白老师:反正你说我不理你就是了,当时我们复的课是写计算机程序的语言,那个时候学程序,我们叫223语言,你可能都不知道。就是说两个位置,说这个位置的数和这个位置数中间有一个运算,加减乘除,都有符号或者计算结果放到第三个位置上面,写了第一个的的位置,这个位置存什么数, 就是写这个位置,下面写的运算符号,然后再写另一个位置的数,结果放到最后的位置上,都是用洞打在纸带上,用01语言描述出来的,打个洞就是1,不打洞就是0。
陈老师:那个时候科大已经有计算机了?
白老师:那个时候有计算机,像放电影的样子,把指令用打孔机打到纸带上输入到计算机里。当时学了一段时间那个语言,后来不准复这个课,就停了。所以说现在计算机的语言跟那时候是不一样的,因为当时学了这个语言,所以我后来就没有再学。
陈老师:1966年秋天开始停课,科大是五年毕业,所以您1968年毕业了?
白老师:1968年毕业。当时是不分专业,按省市自治区分配,每个省几个人,当时我被分到新疆去了。
陈老师:当时得到这个消息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白老师:说实话当时任何想法都没有,没有想同意或者不同意。
陈老师:反正就去了。
白老师:去了,都是一样。
陈老师:当时同班同学也有去新疆的吗?
白老师:我们班两个,一个统计,一个运筹。
陈老师:到新疆的什么地方?
白老师:新疆刚开始分配以后,到新疆有一个分配办公室,在那里报到以后,去奇台县再教育,那里有一个骑兵二团。
陈老师:它和石河子属于一块吗?
白老师:不是,我们那儿是解放军的,不是兵团。石河子是兵团了。
陈老师:那是在南疆还是北疆?
白老师:是北疆。骑兵二团大概是长征当中缴获了敌人一个骑兵团,然后成立的一个骑兵团。他们那有功马(立过战功的马),这些马像老祖宗一样供起来,不能让它干活。我们有几个同学,跑到那把功马偷出来跑马去了,结果把团长气的发大脾气。
陈老师:您主要是做什么呢?
白老师:主要就是学习,没什么事干。1968年冬天,北疆那边,冬天都是一米厚的雪,骑马最舒服的是从马上面摔到雪上面。那个马很聪明,绝对不会往人身上踩,万马奔腾过去都是从你身上跳过去。
陈老师:白先生,您在新疆那里是从1968年到1978年,呆了十年是吗?
白老师:后来分到南疆去了。在部队只呆了14个月,到了1970年4月份,被分配到南疆。然后我回了一趟家,大概6月份到南疆喀什。
陈老师:喀什是比较靠西边是吧?几乎快到边界了,是吧?
白老师:也不是很边界,到边界还有两百多公里。
陈老师:您在喀什做什么呢?
白老师:先在一个煤矿里面当过一段管理员,技术员。我在农场管过柴油机,对柴油机比较熟。一开始我是当管理员,管过一段时间机械设备。
陈老师:在煤矿里,那里做了多少时间?
白老师:那里可能呆了三四年吧。
陈老师:之后呢?
白老师:之后成立新疆喀什农学院,然后就调到农学院了。
陈老师:您去教书吗?
白老师:不教书,当汽车队队长。
陈老师:喀什农学院的汽车队队长,是我们白先生?
白老师:对。
陈老师:您之前会开车吗?
白老师:开车是在喀什的煤矿学的。
陈老师:农学院的汽车队队长,主要做什么?运输东西?
白老师:生活品什么都是靠汽车拉,主要是拉煤,也拉粮食,那么多人的吃喝拉撒睡都要靠汽车。
陈老师:当时农学院也开始招工农兵学员了吗?
白老师:也有招工农兵学员。
陈老师:您那个时候开什么车?
白老师:苏联的嘎斯69。
陈老师:您在喀什农学院开车的期间,有没有时间自己再读一下数学的东西?
白老师:书都丢光了。我从小喜欢动手。我在科大念书的时候,不是学统计吗?那个时候是手摇计算机,非常容易出毛病的,就是哪一个弹簧卡了,出去修一下。修理费用都要20块钱,老师严格控制学生怕出了毛病不能动,但是我从小喜欢动手,你越说不能动,我非要动一下。我们有一个同学叫吴可法的,也是喜欢动手。计算机坏了以后我们俩拿着修,把它修好了,原来弹簧断了,拿着自行车后面的千斤丝弯成弹簧装在里面。不要买那个专门生产的弹簧了。最后就把那个计算机实验室,交给我们俩管,那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事儿了,后来我们把学习用的所有专业书放到那里面去了。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毕业了之后我们才进办公室的,我的专业书什么都没有了。
陈老师:您是带着专业书去新疆了?
白老师:没有,到新疆什么都没有了,在北京的时候就丢掉了。
陈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得到消息可以去考研究生?
白老师:在喀什。我就和办公室的人聊天。都是知识分子,不认识一聊天就熟了。聊天的时候翻各个学校的招生内容,翻着翻着看到了科大招生的。其中比较熟的老师——曾肯成,是李尚志的导师。我念书的时候和曾肯成关系最近。但是他招生的专业,我有科没有学过。他考抽象代数,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是抽象代数,因为我们当时学的是高等代数。这门课从解析几何、抽象代数、线性代数都放在一个课里面,没有一门课专门叫抽象代数。当时我也不知道抽象代数是什么,我以为没有学过。没有学过不能考了。再一个龚昇跟华罗庚一起招,考函数论。我说函数论我也没有学过,这个也不能考。看殷涌泉和陈希孺招的概率统计的研究生,考数学分析、线性代数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这几个可以,还有一个实变函数,这个课我都学过,学的不错。我后来考上研究生后,问赵林城,你学过函数论吗?他说学过,我说我没有学过。他说你怎么可能没有学过函数论?我问函数论是什么,他说就是实变函数和复变函数,我说我的妈,搞了一个函数论把我搞住了,不然那个我也可以考。我实变函数和复变函数学习的是最好的,他们把这两门课程统一叫成函数论,我是两个分开学的,没人讲这两门课统一叫函数论,所以我不知道就不能考啊。就只好考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导师是殷涌泉。我跟他也比较熟。

2015年白老师参加陈希孺院士逝世之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摄影:杨瑛)
陈老师:殷老师在本科的时候教过您吗?
白老师:教过,教在抽象测度论基础上的概率论。
陈老师:从您刚得到消息,到招生办得到可以考的消息,到最后可以考试是多长时间?
白老师:我去的那天大概是3月28号,3月底截止。我问他整个程序。他说我给你一个表,你填上去以后让你们单位盖一个章,写一个介绍信,交给我们行了。
陈老师:您是在截止日期前几天才知道这个消息的?
白老师:我知道消息以后,就回来找我们学校的人事干部,没有请示领导就盖了章。后来学校领导知道以后找这个人事干部,那个人事干部叫刘宗召,说你没有经过领导,为什么同意他报考研究生?他说没有关系,如果您不同意这个邓副主席广招人才的话,你给我写 一个条子,我去写信给科技大学把他报考证书追回来。
陈老师:他很会说话。
白老师:谁敢说这个话?领导说那么算了,报了就报了。就是这样。
陈老师:什么时候考试?
白老师:原来是5月1号,后来好像推到7号。
陈老师:新疆有考场?
白老师:对。
陈老师:一个月时间准备。
白老师:对,幸亏那个时候会抽烟,不会惨了。
陈老师:为什么?
白老师:因为只有一个月时间了,28号拿到通知,29号盖章,30号报上去。我们喀什有一个师专,我们煤矿里面有一个保卫干部,调到师专去。31号我通过他到他们学校图书馆借了一些书,那些书他们都能找到,基本都可以找到,然后就借了六本书回来。考四门课,借了六本书回来,六本书要在一个月里面复习完,书里的习题都来不及算的,没有时间去算,就一个月时间。吉米多维奇习题集大概5700多道题,大概用了3天,就是读这本书,闭眼睛一想这个题会做就翻看下一道题,一看下面一个题会做闭上眼睛就过去了。哪个不会做写一下,写出来有路子了就过去了,想不过去也得过去了。没有时间抠一个题,不会做就不会做了,每个题都想一下。三天就翻过了。第一个考的是线性代数,打开卷子,头脑就热起来了。科大考试习惯是五道题,一道题20分。老师改卷子到最后,一个对号就给你了20分,如果打了一个问号或者叉号,这个题就是零分。最后考试的成绩基本就是0分、20、40、60、100分,不会有零头的,过去一个题最多分两个小题,每个10分,会出现一个10分,考试成绩没有零头的,没有说考78分,不会有这个成绩的。卷子里的五道题,四道题看过,不会做,跳过去。还有一个题根本没有见到过,不知道那个题哪里来的。
陈老师:嗯。
白老师:我想今天要交白卷,头脑发热了。这个时候拿出来一根烟抽,那个时候允许抽烟,如果不允许抽烟就惨了,抽烟了就可以冷静的想一些问题了,总不能交白卷。有一个题没有见到过,大概能够想到一点什么路子去做一下。然后抽了烟以后,有一点想法了,去做做,结果做出来了。做出来了以后,心里就有一点高兴了,一看时间两个小时,过了一个小时,还有四个题,根本一点想法没有,头脑又热起来了,然后就抽第二根烟。按照常规路做,简化简化试试,做了一步以后看出来路子来了,这个大概就是不到十分钟做出来,其他几个一个一个的,心情一好就想出来了。我的代数考了80分,还是比较满意的。
陈老师:后来多长时间以后得到的消息,被录取了?需要去合肥面试吧?
白老师:对,合肥面试,合肥热。我们北方人没经历过那种热,你是南方人吗?
陈老师:我是北京人。
白老师:你见到过合肥热吗?现在好了有冷气,那个时候没有冷气,按照苏淳的说法合肥既有北方的缺点,又没有南方的优点,夏天没有冷气,冬天没有暖气。北方人从小长大我没有冻手脚,到合肥三年每年都冻烂。
陈老师:咱们等一下再说上研究生的情况,现在提一下师母,您是哪个阶段认识的师母?新疆的时候吗?
白老师:对,在煤矿的时候,她叔叔在煤矿开车,她叔叔家里面是穷人,她爷爷去世的早。听我老婆说去挑担子,走了100多里地,碰到一个山泉,喝了山泉水“炸肺”死掉了,她奶奶被亲属卖掉了。她爷爷死的时候,她叔叔和爸爸还是十几岁的孩子,她叔叔可能十二三岁,最后叔叔从老家逃出去了,逃到兰州去了。到兰州,原来是要饭的,一帮小混混,也是打架闹事儿,后来打架的时候被人抓了,碰到一个国民党的军官,一看都是陕西老乡,就问他干什么,他说他们没有什么事儿干。他原来在兰州的时候是国民党一个军服厂做鞋的,可能是和老板闹事儿,把他开除了,然后没有工作。这个军官是青海国民党一个电台的台长,一看都是陕西老乡,说跟我走吧,到我们那去给你个活干。跟着台长到了青海的电台,给他分了一个师傅在那里学开车,大概不到六个月,这个部队台长就起义了,起义了他们跟着到共产党这边来了。到共产党这边来,把他们分到二军,就是王震那里。二军缴获了国民党的汽车没有人开,他叔叔也不会开车,但是毕竟是跟车跟了半年了,哪个是干什么的他都知道,说那么开车吧。就是那样,当师傅开车。开车开的好一点给副军长郭鹏开车,复员以后分配在南疆了。也是分到军垦农场里面,后来成立“反修煤矿”的时候,把他从农场调到我们煤矿来了。我也被调到“反修煤矿”就和她叔叔认识。
陈老师:问一下白老师哪年结婚?您有两个儿子,他们都是在新疆时候出生的吗?
白老师:都是新疆出生的。
陈老师:在喀什出生的。
白老师:对,当时她(白师母)还在岳普湖。
陈老师:您后来在1978年的秋天9月份去了合肥。
白老师:1978年9月份在合肥报道,然后到北京念书了。北京研究生院,殷老师他们都借调到研究生院教课。
陈老师:所以您研究生期间是1978年到1980年?
白老师:对,1978年到1980年底,我的毕业论文草稿,第一稿1980年12月份写的。
陈老师:所以您的导师是殷老师和陈希孺老师。
白老师:对,当时答辩的时候,殷老师出国了,当时陈老师对我的研究已有指导。他上课的时候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两两独立不见得全体独立,书上有的例子就是四面体的例子。陈老师提出说你能不能把它推到N个,两两独立的全体是不独立的,这个问题做出来可以发表。后来陈老师他们组织一个统计的讨论班,统计讨论班上面讲实验设计的时候,讲哈德马矩阵。下面那四行,就是四面体的例子的推广,说任何三个,都是两两独立的以等概率取正负1的随机变量,这三行乘起来等于第四行,四个变量任意三个相互独立,但第四个是由前三个决定的。同理,把n个独立同分布的以等概率取正负1的随机变量,乘起来,仍为正负1。n+1个变量中,任何n个相互独立同分布,另一个是它们的乘积。当然不独立了。换一种说法,假定有n个独立同分布的以等概率取值0、1的变量加起来模2,不仍是0、1吗,很容证明这n+1个变量中任何n个都是相互独立同分布的。这不就是那个四面体例子的推广吗?我和苏淳跑到陈老师家去,大概我们也写了一个草稿,他说这个做出来可以发表,我们写一个草稿给陈老师看,陈老师看了以后很高兴,然后陈老师又说,他说能不能举一个连续的例子,这个连续的例子,原来是零一两点分布,改成在(0,1)区间的均匀分布,加起来取个小数部分不就行了,结果验算一下也对。加起来他等于一个新的,也是一个(0,1)的均匀分布。最后一个等于前面的和,它就不独立了,但是任何两个变量之间都是独立的,其实任何的n个都是独立的,你拿着一个换成任何一个都对,是吧。然后拿着这个例子又去找陈老师。陈老师一看这个(0,1)上的均匀分布,它不是可以反演任何分布了吗?这个例子好,反演任何分布,他说现在不是(0,1)均匀分布,是对任意的分布,他说再推进一步,说给定一个n,一个r,r小于n,任意r个都独立,任意r+1个都不独立。后来我们给他构造了一个例子,从而证明了这个结果。陈老师这次满意了,就让我们写了一个Paper投出去了,投在当时的《科学通报》。《科学通报》是方开泰和陈培德两个人是referee。他们两个又把证明更进一步简化了。并进一步推广到对于任意给定的n个非退化分布,可以构造一个n维随机向量,使得每个变量的边缘分布都是给定的分布,其中任意r个相互独立,任何r+1个不独立。陈老师的问题就推广到这个地步。
陈老师:这个是您发表第一篇文章吗?
白老师:对,第一篇文章。
陈老师:您是新中国的首批博士学位获得者。
白老师:我们为什么能够进首批博士,这个原因是这样的。当时我们正在读林尼克和奥斯特夫斯基,两人合著的一本书,叫《随机变量及向量的分解》那本书。那本书后面提了35个unsolved problems。实际上那个书没有完全读完,读到一半的时候发现35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拿了一个我们把它做出来了。做出来以后,通过王寿仁老师推荐发在《中国科学》。我拿博士之前还没发表。因为我们科大数学系的老师,都给研究生院教课、代课,所以他们把学生都带到研究生院去了。合肥科大也有研究生院,抓不住我们的学习情况,说这些学生哪里去了,政治干部到年终有一个总结,思想总结、业务总结都有很多表要报,结果数学系什么都没有。所以研究生院对数学系发脾气,说你们数学系研究生怎么带的,年终总结什么消息都没有,你们怎么这么不负责?这个时候数学系负责人叫陶茂颀,陶茂颀是北大毕业的,后来调到科大的。当时他是数学系代理系主任。之前系主任龚昇当了副校长。陶茂颀当代理系主任,跑到北京调查我们学习情况。一调查发现我们几个人,赵林城、我都有paper了,然后他回来就拿着这个当石头砸(合肥的)研究生院,你批判我们不会带研究生,我们的研究生都写出paper来了。

1982年,白志东、赵林城在参加中国数学会香山会议期间与他们的博士答辩委员会委员合影。从左到右 严士健,白志东、魏宗舒,江泽培、陈希孺、吴文俊(非答辩委员)、张尧庭、王寿仁、成平,赵林城
陈老师:对。
白老师:说我们怎么不会带研究生,你们研究生带的怎么样?有什么成绩比我们好?你有成绩研究生院就不担心你了,他也不是为了和你吵架,然后他们把这个东西报到科学院去了,我们研究生有这个成果,像我解决的那个问题的提出者林尼克和奥斯特洛夫斯基都是世界名人,很有名的人。解决名人书上没有解决的问题,你知道中国最喜欢讲解决哪个名人提出的问题。
陈老师:猜想。
白老师:对。当时是1980年5、6月份,上面下过一个重要文件,说不是已经招了这些研究生吗?特别优秀的少数的授博士学位,大概半数左右可以授予硕士学位,一般的就是作为研究生毕业就行了。当时就是这么定的,特别优秀的是博士,一般优秀的就是硕士,再差就是研究生毕业,不授学位。那么我们有paper的,这几个人先做博士试点。
陈老师:18人被授予了我们国家首批的博士学位。
白老师:当初没有那么多。当时1983年5月25日之前授予学位的参加赵紫阳(当时国务院总理)的接见。那个时候苏淳他正好是截止那天答辩的,还有一个是1月份答辩的,但1月份答辩的时候学位委员会没有及时讨论他的问题,拖到了苏淳答辩之后。学校学位委员会在苏淳答辩之后当天开会,讨论把他们俩个一起通过,是这样的。按这个文件不行了,你5月15号,中国的文件讲不清楚,5月15号以后,5月15号到底包括在前面还是后面搞不清楚。
陈老师:对。
白老师:然后给中央打报告,科大打报告是给三个人,一个是给邓小平,另外一个给胡耀邦,另外一个给叶剑英,给这三个人打报告。因为科大党委书记杨海波和胡耀邦是好朋友,他们都是共青团中央的。
陈老师:对。因为这个报告牵扯到山东大学的于秀源,于秀源也是这个时期以后的,那么你苏淳可以加进去,他也可以加进去。
陈老师:对,所以他也上了。
白老师:他也上了,还有王建磐,华东师大的。
陈老师:白老师,我们接着来。上午我们说到您是全国首批的十八个博士之一。博士毕业以后,您就留到科大工作。

1985年中国首批博士合影,苏淳(右二),白志东(右四),赵林城(右七),洪家兴(左三)。

2010年中国首批博士合影,苏淳(右二),白志东(右四),赵林城(右七)
白老师:对。没有毕业就回科大工作了,我们是1981年3月份就回到科大去了,殷老师开一个课我给他当辅导。后来他出国了,我替他接着讲。
陈老师:就在合肥了。
白老师:1982年5月份,国务院下的文件,5月15号答辩。
陈老师:所以您在科大教了三年书,1984年去匹兹堡?
白老师:对,工作了三年。
陈老师:您在博士期间写了19篇论文是吗?这个是很高产的。
白老师:15篇。都是国内发表的。
陈老师:也都应该是《中国科学》这类杂志 ?
白老师:《中国科学》、《数学通报》、《数学学报》和《数学年刊》。
陈老师:这是很了不起的。
白老师:所以当时一看简历,Krishnaiah(匹兹堡大学)立马要了我。
陈老师:您之前提了殷老师,他是1981年去的美国?
白老师:对。
陈老师:然后他给你介绍到匹兹堡?
白老师:对。
陈老师:您的老师殷老师也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吗?
白老师:殷老师是北京人,虽然是在沈阳长大的,但是很长时间在北京,他说一口标准的北京话。他讲课的时候可以弄得很多学生笑,但他不笑,但是他说话很幽默的,他讲复变函数中解析函数的延拓,他说这里有一族解析函数,这里也有一族另外一个解析函数,然后说画了好几个大圈,然后这个相交的地方是一样的。那么就存在一个解析函数,每个和每个是一样的。他就画一个一个圈,画着画着逗笑了,他也不笑,他说话有点东北味,也有北京普通话味,他经常把很多学生逗笑。
陈老师:所以您1984年也去了匹兹堡?
白老师:对。
陈老师:您在那呆了多少时间?
白老师:在匹兹堡呆了四年,直到老K去世。我们给Krishnaiah起了一个中文名,叫他老K。
陈老师:他组织能力很强是吗?
白老师:我和陈老师开过一个玩笑,我说你觉得你和Krishnaiah的能力你们谁厉害?他说Krishnaiah的能力怎么能和我比,我比Krishnaiah强多了。我说有一条你肯定不能和Krishnaiah比,他说哪一条?我说他这么多人(研究人员,访问学者),我在那里最多的时候Krishnaiah有十三个visitors,这十三个visitors每个做不同的领域,不可能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我知道Krishnaiah不做这个领域,但是他给这些年轻人制定题目,而且他给的题目正好适合这个人。我对陈老师说,你指导你熟悉的领域可以,你能不能指导你不熟悉的领域?这一点你肯定比不上Krishnaiah。陈老师想想,这个确实Krishnaiah厉害。
陈老师:当时Krishnaiah在匹兹堡Center for Multivariate Analysis,是吧?
白老师:嗯。
陈老师:这个当时在世界上很有名的,我当时念书的时候也都知道这个中心。
白老师:到最后他快去世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感动。令我特别感动的是他的夫人。老K到最后鼻子里插着管子,滴着营养液一点一点往里面滴。我们有一个台湾的学生叫孙永年,他有车,帮老K管计算机的。老K每个礼拜要那个秘书整理各种文件,需要他签字,需要他看的,让他带过来。我们两个把各种信件和文件送到他家,他平均一天发四十封信,一个礼拜好几百封信了。他老婆一边掉眼泪一边给他读,读完了以后他说哪个地方需要修改,他老婆就帮他改,回来以后秘书重新改那个信,这个信他说可以了,他老婆就帮助他签字,然后信封起来,带回来,让秘书发出去。那个样子了,他老婆还得要帮助他处理来往信件以及《多元分析》杂志编辑部的事情。
陈老师:Professor Krishnaiah是非常敬业的。
白老师:他死一个星期之前,我们到他家就是这样,再过一个礼拜人就没了,他老婆还帮助他读那些信。
陈老师:当时他还是director。
白老师:对,他是director。
陈老师:后来Professor C. R. Rao 什么时候加入了匹兹堡?
白老师:他1980年60岁,在印度退休后就来到匹兹堡。从很有名的印度统计所,也简称ISI。

白老师跟C. R. Rao 90岁生日的合照
2003年摄于新加坡
陈老师:您在匹兹堡四年研究方向和在科大有没有比较大的变化?
白老师:比较大的变化是我们做过一个给心脏造影。对于固定的物体,CT需要做360度的投影,实际上就是一个傅里叶反演,每个方向上的傅里叶都知道,这个二维空间上的傅里叶就知道了,傅里叶反演就能把形状描绘出来了,这个CT原理就是这样。这样一个个投影过去,这一个东西是360度投影都照出来,物体的形状可以构造出来。
陈老师:对。
白老师:这个东西对动的东西不行,心脏在不同的时候是变化的,这个方向和那个方向处于不同的位置,你照出来的图形不是心脏即时的图形。同时的两个照片,所以互相垂直两个方向照的,这边照过去,那边照过去,心脏的型可以构造出来。这个问题是西门子公司提出来的,匹茨堡医学院的一个印度教授申请到的一个很大的grant,最后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大。就是利用这个grant,买了250万美元的机器,从西门子买的,好像买了四台,250万一台的机器买了四台。然后他还有其他科研经费,他是每三个月给我们多元分析中心40万美元,一年是160万,我们发的薪水就是从这个钱里面出。
陈老师:这笔钱很大。
白老师:他给了这个钱,实际上是after overhead以后的,他还要给学校交60%的overhead。
陈老师:加上overhand每个季度是一百万。
白老师:他三个月就得一百万,一年就是四百万,光我们就要四百万,你说他有多少钱。我在美国做的最大的工作就是这个心脏的构造问题,通过两个正交投影,他不是整个心脏,是左心室,左心室是全心泵血的力量最大,很多人的病和左心室变化有关系,要把这个左心室形状搞出来,血液里面打一些药之后照的照片,用在一个固定时刻照出来的照片来构造出心室的形状来。
陈老师:所以你们弄出来一个算法帮助他估计这个。
白老师:对,我们弄了一个算法。结果台湾的学生负责计算理论上的部分,我给他出主意怎么算,当时赵林城在那。
陈老师:这个是不是您相对来说比较早的做应用的文章?
白老师:到美国最大的好处是人家有钱支持这个研究,国内现在没有发现中国是不是有这种机构给这种钱。西门子公司光给匹茨堡大学,不知道多少钱了,不说几千万,肯定多少亿了。
陈老师:对,今年(2018年)春天斯坦福的Professor David Donoho,他在清华给了一个talk,他就是专门讲西门子的设备,做imaging的。和他后来做的一些高维的shrinkage的研究是有联系的。所以您还是非常enjoy您四年在匹茨堡。
白老师:我对那四年做这些工作蛮感兴趣的。
陈老师:后来到1988年您去了哪里?
白老师:1988年去了Penn State,因为1987年,老K去世了。老K去世以后在匹茨堡的印度人都呆不住了,美国人排斥这几个印度人。Bimal Sinha 搬到巴尔的摩 UMBC,C. R. Rao 搬到 Penn State。还有一个Subaraniam搬到北卡温斯顿。印度人都跑掉了。
陈老师:C. R. Rao把Center for Multivariate Analysis搬到Penn State去了吗?
白老师:对,C. R. Rao 也把我带到 Penn State。
陈老师:看来Krisnaiah的领导力很强,他在时,别人不敢动他的团队。
白老师:对。Krisnaiah不怕和别人吵架,他当初和美国人当面都吐口水的,很强势的。
陈老师: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很有凝聚力的领导者。当时那个《多元统计》分析杂志是不是也在匹兹堡的Center里面。
白老师:对,就是在Center里面。
陈老师:这个杂志有悠久的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创刊的?
白老师:是C. R. Rao搬到匹兹堡之前就创立了,大概是70年代。
陈老师:刚才想起来您和Babu做了一些 Edgeworth expansion的工作,那是在Penn State?
白老师:那是在Penn State的时候。
陈老师:那个工作的影响挺大的,因为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看到您的这一研究。
白老师:我在那里做edgeworth expansion,最大的贡献就是一个多元分布,他联合起来,比如说有一个变量是离散的,edgeworth expansion的Cramér条件就不成立了。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条件,Rao起了一个名字叫Partial Cramér条件。不要整个的特征函数满足,只要给定几个变量,条件分布的特征函数取绝对值再取期望后满足那个上极限小于1。如果有几个连续变量,把离散变量放到条件里面去,他的条件分布是连续的就行了。
陈老师:这个推广了Edgeworth expansion的条件。
白老师:我觉得在那最大的贡献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moment是最小的minimal moment条件,这个条件是从你老板(Peter Hall)那来的。他不是做了一个T化统计量(Studentized statistic)的Edgeworth expansion,这需要在K阶矩的条件下。他的关键问题,有一个变量的导数的条件,在某一个方向的导数等于零,在那个导数为0的方向上面就可以Taylor展开到高阶了。例如说m次方,这一项的贡献将是n-m/2,这一项的k/m的贡献将是n-k/2,故渐进展开只要这一项的k/m阶矩就够了。按Bhattacharya and Ghosh 1976年的结果,这一项也需要k阶矩存在。这样一来,我们对那个变量的moment的要求,就是最小的了。基本上就是把他的T化统计量最小矩要求推广到更一般均值函数了。
陈老师:然后您去Penn State 两年,1990年去的Temple?
白老师:对,我去Temple是1990年。
陈老师:在统计系?您在Temple呆到哪一年?
白老师:是的,呆到1994年。美国共呆了十年,匹兹堡四年,Temple四年。
陈老师:在这个阶段,我看您第一篇大维协方差矩阵paper也是80年代就发表了。
白老师:1983年开始有了。
陈老师:所以在科大就开始做这个了。
白老师:那个是殷老师给我写了一封信,就是说Wishart分布的最小特征根几乎处处大于一个正数,因为他们要做一个相当于F矩阵的谱分布的存在性,他需要这样一个结果。当时殷老师给我这个问题,我想办法给他提供证明。后来和殷老师和Krisnaiah我们三个人联名发了一篇paper。我当时收到殷老师信的时候是1982年,那个时候正好回新疆,我还没有出国。在新疆想出来的办法。当时把那个球分成一块一块的,算独立的那些。最小特征根X’AX取最小值,利用这个概念分成小块算的最小值,用这个方法把它整出来了。
陈老师:您在九十年代左右,有好几篇文章发表在Annals of Probability上面。
白老师:对。
陈老师:后面有一部分工作是在匹兹堡做的,还是在Penn State的时候?
白老师:有的是在匹兹堡,1993年以前发表的是在匹兹堡做的,有一些实际是去Temple之前就开始做了。
陈老师:是这样。
白老师:有一些在Temple以后,比如发现谱分布收敛速度的问题,是到Temple以后做的,是帮助别人审一篇文章,一个乌克兰人叫Girko,在苏联是名气非常大的一个数学家,他写了一篇文章。但是他好像是学物理的,随机矩阵这些东西,不管多难的他都做,他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在苏联太有名了,所他的文章会发表到一些很厉害的杂志上。他的文章都是“来稿照登”的,不管对不对,也不审稿。就会出现一些错误。但是他写的文章,很多人看不懂。我在Temple有一次接到Annals of Statistics(AOS)的一个副主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他有Girko的一篇文章问我想不想帮他审稿。我说可以审稿,但读Girko的文章有两个困难,一个困难他写的文章是类似English words with Russian grammar。
陈老师:俄国英语。
白老师:俄文是有变格变位的,名词可以变成形容词,谁形容谁这个关系是很清楚的。变成英文以后,一个一个名词联在一起,甚至十个名词联在一起,哪个修饰哪一个你自己去猜。他可以把十个名词联成一串,他俄文是变格变位关系很清楚,它把它翻译成英文以后,一个一个都变成名词了。我说还好,我学过一点俄文,可以猜出来大概什么意思。我说另一个困难,就是他经常把这个实数对的不等式用在复数的情况下。复数不对了,但是实数是对的,他把这个不等式拿来用。他说还有这样的不等式吗?还有实数对复数不对的吗?我说还好,我桌子上就有他的一篇paper,我给你读一下,你记下来看看这个不等式。然后我把这个不等式读下来了,我说这个就是实数对,复数不对,他的文章就用了。这是一个明显的事情,复数不对,他一看就知道了,他说这样算了,不用你审稿,我把这个paper拒了算了。这个人(Girko)当时有很多点子都是对的,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圆率的问题(circular law)。
陈老师:对。
白老师:这个问题就是1984年Girko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发表以后,美国人谁都看不懂,就是在美国引起了一个很大的问题。1984年我去美国以前,开过一个随机矩阵会议, Charles Neyman这个人在数学界名气很大,当时在 Arizona大学(图桑),就是后来殷老师去的那个地方。他说谁看懂了给我讲一下,路易斯安纳那边的一个教授说他看懂了。Neyman说好,我邀请你到我们这边演讲。然后Neyman把那个人弄到图桑去给他们讲。等到了图桑后,那位说还有一点问题没有看过去,我要再看一下。Neyman说好,我给你访问教授,你在这儿呆一年,什么时候看懂了什么时候给我讲。过了一年以后他说还有问题,他说那么我给你tenure留在这儿得了。结果那个人就留在Arizona大学了。在那呆了三年说对不起,我看不懂。
陈老师:我也不问您是谁了。
白老师:我也不知道是谁,反正殷老师告诉我的,和殷老师在一个系。
陈老师:殷老师后来到Arizona大学去了?
白老师:在Arizona呆了三四年,后来他自己找工作,在马萨诸塞州的Lowell大学找到正教授职位,在波士顿北边大概20~30公里,那里给他教授他就去了。同时,密歇根州有一个什么大学,给他副教授他没有接受。
陈老师:您能讲一下离开Temple的原因吗?当时您非常有名,是我们中国第一批博士,我们学统计的,对您是非常敬仰,您后来离开Temple对我们华人来讲,包括对于美国人来讲都是震动比较大的事情。您能不能讲讲这个方面的事情,如果不介意的话?
白老师:Temple那个学校,有一个特点,很容易拿到他的offer,但是很难拿到他的tenure。我很多学生也是在那呆了一两年就走了,后来我们在那里很多同事,都是拿不到tenure走了。
陈老师:它是在商学院里面吗?
白老师:在商学院里面。我去了以后有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就是罢工。当时不知道是政府还是什么单位去调解,没有调解成,最后是政府下了法令,这个罢工必须结束了,然后就结束了。
陈老师:罢工多少时间?
白老师:从我去了的时候,罢到10月份。9月份开始上学,罢到10月份,我去以前就罢工,罢工以后,就是这个政府调节不了,美国有一个仲裁什么的。
陈老师:法院仲裁是吗?
白老师:对,裁定这个罢工不合法,必须让这些老师去上课了。罢工对商学院的损失是最大的。1986年罢工,1990年又罢工,中间不到五年的时间,很多学生两头都赶上了。Temple损失了大概30%的学生,学生跑到别的学校了,其中90%的流失都是商学院的,商学院多一半学生都跑掉了。后来我们没拿到tenure,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一下钱损失了很多。
陈老师:所以后来您就去了台湾的中山大学。
白老师:我去台湾是因为台湾中山大学的黄文璋,你认识他吗?
陈老师:我认识。我们二十年前在昆明开泛华会见他,后来几次开会都见到过他。您在台湾后来呆了总共几年?
白老师:呆了三年多。
陈老师:您在台湾期间主要研究哪些问题?
白老师:我比较多的paper是在台湾做的。
陈老师:您在台湾呆了三年多,后来怎么去的新加坡了?
白老师:当时认识路易斯(陈晓芸Louis Chen)就是在台湾开过一次泛华会,在泛华会上认识了路易斯。然后我给路易斯发一个电子邮件,说我想找工作,问他要不要。路易斯回信说我们这里已经是满员了,但是搞统计的我们还要,他说你赶紧写一个申请。
陈老师:这是1997年?
白老师:1997年的事儿,我1997年去的。
陈老师:很顺利过了?
白老师:对。为了签证的事情,给路易斯找了一个大麻烦。因为我的大陆护照,有效期不到六个月,我到新加坡签证,新加坡说你的护照不够半年有效期不能签证。不能签的话,台湾也不能用大陆护照。当时路易斯的弟弟是内政部部长。他指示让这个人先进入新加坡,新加坡有中国大使馆去延长护照,然后通知移民局,移民局写了一个批准信。凭那个信可以进来了。正好赶到礼拜六,我到大使馆延护照,使馆说那个系里面接受我必须有一个证明才行,你不在新加坡怎么开护照。我找路易斯给我开证明。路易斯正在听学术报告,我一找他就出来了。做报告的是一个美国人,给校长发了电子邮件,说路易斯太不尊重我了,我做报告的过程当中他跑掉了,向校长告了一状。校长说你怎么能这个样子,路易斯和他讲我们招这个人的中国护照需要延长,中国大使馆需要开证明,我给他开。那你去给这个老外去解释一下,不然他就会对我们学校有意见。如果我礼拜六不延护照的话,到礼拜天一关门就延不上了,那么就要回去了。
陈老师:您一开始在新加坡国立数学系?
白老师:一开始是数学系,他们准备成立统计系了。为什么说数学系是满员了,但是搞统计还要,因为要成立统计系。
陈老师:NUS统计学的创系系主任是邢泰伦(Tailen Hsing)?
白老师:是的。
陈老师:你在新加坡以前认识他吗?
白老师:以前不认识,新加坡认识的。
陈老师:那个系什么时候成立的?
白老师:1998年。
陈老师:您加入后不久就成立了。
白老师:对。
陈老师:您在新加坡呆了,也有十几年?
白老师:对。
陈老师:我是2000年加入的,和您做了三年半同事。还是很难忘的。您到新加坡以后,研究方向来有没有变化?
白老师:原来我是没有固定的方向的,我碰到什么问题做什么问题。到了新加坡以后和胡飞芳做adaptive design,做了一些东西。从他走了以后,我基本固定在随机矩阵里面了,那个时候随机矩阵也热起来了。从那以后没有再干其他方向了。
陈老师:在随机矩阵研究方面您是非常高产的,是我们非常敬仰的学者。您做了很多领域,只要有新问题就做。您能不能给出三个贡献最大的或者最喜欢做的领域?
白老师:我觉得我贡献比较大的就是随机矩阵。
陈老师:这个时间跨度也很长,1983年的第一篇文章,现在还在做。
白老师:对。原来的时候,仅仅作为一个数学问题来做,作为一个难题来做的。学数学的对难题有兴趣去抠,到后来逐渐掌握应用了,才真正对它感兴趣,所以我2004年的工作,做的关于谱分布函数的中心极限定理,那个可以用到统计里面的,这个问题是我提出来的。后来还有一个用的比较多的就是郑术蓉那个,郑术蓉把他推到F分布。因为统计里面F分布,这个F矩阵比样本协方差矩阵用处更多,总体协方差矩阵换成样本协方差矩阵就变成F矩阵了,所以这是郑术蓉做的这些工作。我把这个做的基本想法,告诉郑术蓉,郑术蓉不到一个月,她花了大功夫读懂了,把这个推广出去。后来她这个结果发表在法国的AIHP(Annales de l'Institut Henri Poincaré, Probabilités et Statistiques)上面。
陈老师:就是法国科学院的期刊。
白老师:对。
陈老师:您实际上在高维统计热起来之前,1996年就在Statistica Sinica上面发表文章了,高维二样本检验的工作。
白老师:那篇文章是先投的JASA,JASA没有接受。然后不知道怎么让吴建福知道了,他说给我,我要。
陈老师:那个工作是在后来高维均值检验里面影响非常大的。
白老师:对,那个Saranadasa是我在Temple的学生。我在Temple的时候,我指导他论文,当时他发现了Dempster的一篇文章(Dempster,1958)。
陈老师: Dempster检验那篇。
白老师:对。Dempster就同一个问题发表了两篇文章,他一个是58年的,一个是60年的,两篇文章,一个发在AMS,另一个是发在Biometrika。我不知道一篇文章可以发表两遍。我没看出来差别在哪。
陈老师:我得看一下,我就看了他一篇文章,看了他的Annals的文章。
白老师:然后就是,这个文章被Saranadasa找出来的,his first name叫Hewa,长的黑黑的黑娃,他是斯里兰卡人,他是Temple系主任的学生。
陈老师:那系主任叫什么名字?
白老师:Ragu,就是Raguavorao。他一般写的简称就是D. R. Rao。
陈老师:D. R. Rao!
白老师:他说 next to C. R. Rao
陈老师:OK。Ragu是他的小名。所以当时他是把您招过去的。那篇paper一开始JASA没有被接受?
白老师:JASA没有接受。
陈老师:这篇文章影响非常大,现在引用率非常高,很多做高维的都在引,包括我自己的工作也是看了您的文章之后,当时是在新加坡的时候,我有一次在Tearoom里面,您把您paper的抽印本,就是有cover的那种,当时发表文章,还买期刊的抽印本。所以我就看了那个,看了那个以后跟秦英莉,您的一个学生到那里给我做学生,我们就开始做那个,后来我们也发了一篇文章。白老师您现在已经在中国了,您是哪一年开始到东北师大来的?
白老师:我是2002年。
陈老师:又回到国内,也是离开了有差不多20多年。
白老师:我到东北师大来,有一个原因。我不是国外呆了20年吗?如果我回国以后这20年工龄不算,一退休我就没有钱了。当初最早让我回来的是华东师范大学的茆诗松。
陈老师:对。
白老师:但是让我回来的话,我退休以后生活要有保证,我才能回来。学校两个选择:要么承认我出国时间的工龄照算,要么别让我退休。别的学校都做不到,华东师大做不到,同济大学做不到。
陈老师:您是不是和北大联系过?
白老师:没有和北大联系。北大是刁先生和我讲过,那时候你还没到北大,他说我想去他介绍我去。我后来看他三年一延期,就没有想到那里去。因为史老师(史宁中老师)和我说,他说你这个工龄不好办,国家没有这个文件。至于说不退休,我们有荣誉教授可以不退休,凭您的学术成就,您在东北师大是可以当荣誉教授的。
陈老师:史老师还是很有办法。
白老师:后来国务院下文件,所有的院士和教授都要退休,没有办法了。
陈老师:说起来院士,您是哪年当选了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的?
白老师:1989年。
陈老师:您是哪一年选上IMS fellow的?
白老师:1995年。因为我们过去没有关注这些,后来到了台湾以后,黄文璋提出你为什么不申请一个IMS fellow,然后他和赵民德讲了,赵民德推荐了我。
陈老师:我想您之前申请肯定没有问题。白老师,您是从1978年离开新疆到科大读研究生,之后这几十年您在学术上是非常高产的。1978年到今年正好是40年。您也看到实际上1978年的统计学和现在2018年统计学还是很不一样的,您能不能来comment一下,您怎么看这个
白老师:我和台湾的赵民德很熟,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台湾“中研院”的统计所所长,我们经常一起开玩笑,他说你做的根本不是统计,你们是数学,做大样本的就不是统计,统计就应该是小样本的。他谈这个话也没有错,当时大样本收集不到,第一收集资料就是一个问题,你往哪里存,你收集几百个资料了不起了,你收集几十万、上亿的资料往哪里存?和今天不一样了。所以我受到很大的影响是计算机的影响,我做统计学感觉印象深刻的,第一个是M估计,第二个是Bootstrap。M估计是Huber发明的,另一个是Efron。但是这两个都是70年代兴起来的,为什么70年代兴起,那个时候计算机突然发展,应用到处都是。
陈老师:对。
白老师:我们之前做Bootstrap,造一个随机数怎么造呢?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摸球,找一个袋子来摸球,用十个球,装进一个袋子,标上0-9,摸出来一个就是一个随机数,摸两个就是一个二位数,三个是三位数,四个是四位数。想造一万个四位的随机数,要摸四万次球,什么样的袋子都让你摸烂掉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翻书,翻到最后一位或者最后两位数,要比较厚的书。这个也是伪随机的。你如果造一个随机数的话,造一万个四位的随机数,新华书店都被你翻烂掉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儿。但是现在变成很容易的事儿,不是真正的随机数,是一个伪随机数。这个事情为什么能发明起来,因为过去做不到,现在可以做到了,所以M估计和bootstrap就兴起来了,Bootstrap是Fisher提出来的叫resampling。Fisher的名气比Efron 大多了,但是Fisher提出的东西反而没有人理睬,号召不起来,就是因为没有计算机的帮助,所以做不到。等有了计算机这两个东西才推广起来了。后来我到了Temple之后,Hewa做的那篇毕业论文,Ragu给他(Hewa)题目让他做一些模拟,他(Hewa)就是用Fisher统计量,他有一个Sn矩阵的逆在里面,X均值减去Y均值的转置乘以Sn的逆再乘以X均值减去Y均值。
陈老师:对。
白老师:当维数比较大的时候,没有那个inverse反而会比较好一点,然后他(Hewa)做simulation验证是对的,然后Hewa就急了,说这个理论部分怎么办?Ragu说我们下半年就会请来一个mathematician。所以我到了Temple以后,帮助解决Hewa这个问题。他的问题提醒了我,维数大了以后多元分析的理论是有问题的。
陈老师:对。
白老师:尤其后来找到Dempster的那个问题,提出一个新的检验比他的好。所以我就提出那个问题之后,吴建福说什么也不让我写那句话(“维数大了以后多元分析的许多定理都需要再检验。”)。
陈老师:您把这个说一下,现在读者听起来可能挺有意思。
白老师:我就写的When the dimension is large, then almost all theorems in multivariate analysis need to reexamine。吴建福说你这个话太伤人了,我不能给你刊登,登出去到时候别人都会骂我们这个杂志的。
陈老师:这在当时还是有一点超前。
白老师:对,那是1996年到台湾以后发表的,到了2006年十年才引用五次。
陈老师:是吗?
白老师:其中还包括三个是我自引的。
陈老师:对。
白老师:说明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人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只有少数几个人认识到这个问题,例如O. Ledoit 和 M. Wolf。然后到了后面的2011年,我报国家二等奖的时候,2012年拿到的。四年新的引用是30多篇了。后面的四年比前面十年多了四五倍,现在增加的速度就更快了。我前几天看到快有300多篇引用了。越来越被人重视了。
陈老师:那篇paper是非常重要的。
白老师:当时那个话吴建福不给我删掉的话,它的贡献就大多了。前些年(2010年)在天津开概率统计年会,吃饭的时候和吴建福坐在一起,我和他抱怨这个,他说我今天仍然不让你写这个话。当时不让你写,今天还不让你写。
陈老师:他有他的考量。
白老师:他说有人一辈子做多元分析,你说人家做的都是错的。我说我没有说都是错的,我说要重新检验reexamine,我说还有一个条件,the dimension is large。没这个条件,dimension小的时候他们是对的。
陈老师:白老师,您现在在中国,在自己的祖国,然后您现在对年轻的统计学者,还有现在的学生,有什么话要说的?不只是对中国,包括对世界上的年轻人,您有什么advise?考虑到您的这种非常rich experience,您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吗?
白老师:在中国,大概最差的一个问题就是应用背景的问题。我们招人、招学生、作报告什么的,我经常问这个问题——你怎么把你做的研究领域应用到一个实际的例子?好像很少有人能清楚的回答这个问题。后来高夯说了一句实在话,你自己不知道怎么用,说明你这科没有学好。
陈老师:高夯是?
白老师:高夯,我来的时候是我们系的系主任。他原来是东北师大研究生院院长。他说这个话我是赞成的。你自己学的东西不知道哪里用,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用,你让讲他的领域的东西他讲的头头是道,但是你让他讲应用他就不知道怎么讲了。在美国就反过来了,他会讲应用的东西,不会讲理论的东西。你讲的太理论了他不愿意听了,你讲应用的他倒是有兴趣。在中国你让学生把学的东西和应用联系上,他就说不行。中国学生有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的学生,外国的学生,应该加强理论的学习,但是理论学习也要和实践应用结合。我做随机矩阵,我觉得我真正贡献最大的,为什么我说的那个04年的文章(Bai and Silverstein, 2004,The Annals of Probability, 32: 553-605)呢?我真正能够同似然比检验联系起来,你过去的时候似然比检验用Wilks定理,似然比检验在一定条件下渐近于卡方分布,自由度就是参数个数,当参数个数一大了逼近就不好了,所以做了很多工作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我经常用一个开玩笑的话说,金庸小说有个包不同,你知道吗?
陈老师:包不同?
白老师:不管你说什么,他都说“非也,非也,就是你不对,你说的不对”。现在统计无论你的假设是什么,不管你hypothesis是什么,统计检验永远是拒绝的。那么就是说在这个维数比较大的时候用Wilks定理逼近那个似然比检验。最后的结果一定是reject。
陈老师:是的。
白老师:这个肯定不好。现在有了这个随机矩阵,修正的似然比检验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陈老师:您好像2009年也有一篇AOS的paper讲这个?
白老师:对。协方差矩阵线性谱统计量的中心极限定理,是2004年的文章,郑术蓉的F矩阵,好像是在2012年发表。实际上2009年的paper就用了这两个结果。这个老外一看中国人写的文章,首先批评你英文不好。
陈老师:是这样。
白老师:有的时候写的骂人骂的很凶的,说写的这么烂。实际上在新加坡花了六个月的时间请人帮着修改,投出去照样被人骂。到最后了,把paper拿给何旭铭看,文章中感谢了何旭铭,就不说了。何旭铭看了再批评你英文不好就不行了。大概他们不敢骂何旭铭英文不好。
陈老师:白老师,关于研究问题的选择您有什么建议?
白老师:过去我在新加坡提出一个论断,我说一个人要有两把尺子。一把尺子量量这个问题多难,一把尺子量量自己本事有多大。你自己本身这个长度比问题长度还长,那么你肯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抓住不放,不解决了不罢休。有一些问题一量,根本克服不了这个问题,你就别touch。你是浪费时间的。
陈老师: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
白老师:我做研究,我就首先考虑自己有没有本事解决这个问题,没有本事解决,当然就不要考虑了。这个想法和匈牙利的Erdos比较像。看见3X+1那个问题之后,很多人说这个问题比哥德巴赫猜想还难,Erdos考虑这个问题不到两个小时,最后他说了一句话,“解决这个问题的mathematical tools(数学工具)还没有准备好(not ready)”,所以他不考虑了。这个是做研究最明智的,解决不了的问题不要浪费时间了。
陈老师:白老师,您遇到过最难的问题是什么?您有觉得没有能力解决的的问题么?
白老师:花时间最多是圆律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但是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从1984年到美国,到1997年发表,经过了十三年,这个是花时间考虑问题最长的一个。当然,我不是只考虑这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有时间就想想,有时间就想想。我专门考虑这一个问题就不行了,不能把时间都花在这一个问题上。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其他还没有碰到一个问题我认为可以解决却解决不了。3X+1考虑过一下,但是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思路了,听了Erdos这个话,就不考虑了。所以我在新加坡提出interesting research 和survival research。路易斯说你怎么能够做survival research,你应该做interesting research,我说我三年没有publication,你肯定不给我延长contract,我吃什么喝什么?我怎么活?我必须保证自己可以活下去才能做research,只有我保证survive research能够continue的时候,我才能去做那个interesting research。当时路易斯没有办法反驳了。
陈老师:那么您发表的二百篇文章里面,多少是interesting research,多少是survival research的?
白老师:interesting research大概不到五分之一。
陈老师:您说不到五分之一?
白老师:应该不到五分之一,包括关于心脏的两篇文章,关于随机矩阵几个应用的文章也是。其他的问题,关于M估计,碰到这个问题了就去做一做。
陈老师:但是,也不是为了survive。
白老师:但是和survive有关系,我有了publication的话谁都想要我。你说你没有publication谁要你?
陈老师:嗯。
白老师:我没有那么多publication,史宁中也不是跟我关系好才要我的。
陈老师:那是。
白老师:当然有一些东西,可能对别人是属于有兴趣的。
陈老师:对。
白老师:我们有时候,可能当时一时兴起开始想这个问题。
陈老师:比如说您和Professor Babu做的Edgeworth expansion,您觉得这个是out of interesting or out of survival。
白老师:当时不存在survive的问题,当然我的publication也不少,有一点interesting,但是不是说我只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这与Peter Hall的文章有很大关系。他提出他在T化统计量里面,用了minimal moment condition,我想办法把这个推广了。
陈老师:白老师,再问一下您私人的问题,您有两个儿子。他们现在都在做什么工作呢?
白老师:老大是学的EE,他念书的时候EE正好是最不景气的时候,我说现在不景气,毕业以后可能就景气了,结果他毕业拿到博士以后,变得很热门了。现在在天普大学当系主任呢。然后这个老二,老大说我没有学老爸的专业,你学老爸的专业吧,不要让老爸后继无人了。所以白刚学的统计。但是他不愿意教书。
陈老师:我在新加坡见到过他几次。
白老师:他毕业以后就想尽办法跑到FDA去了。
陈老师:您现在也是爷爷,您现在有几个孙子孙女?
白老师:有三个孙子。
陈老师:真好。
白老师:我们家姓白的都是男的。白利生了一个儿子,白刚生了两个儿子。
陈老师:谢谢白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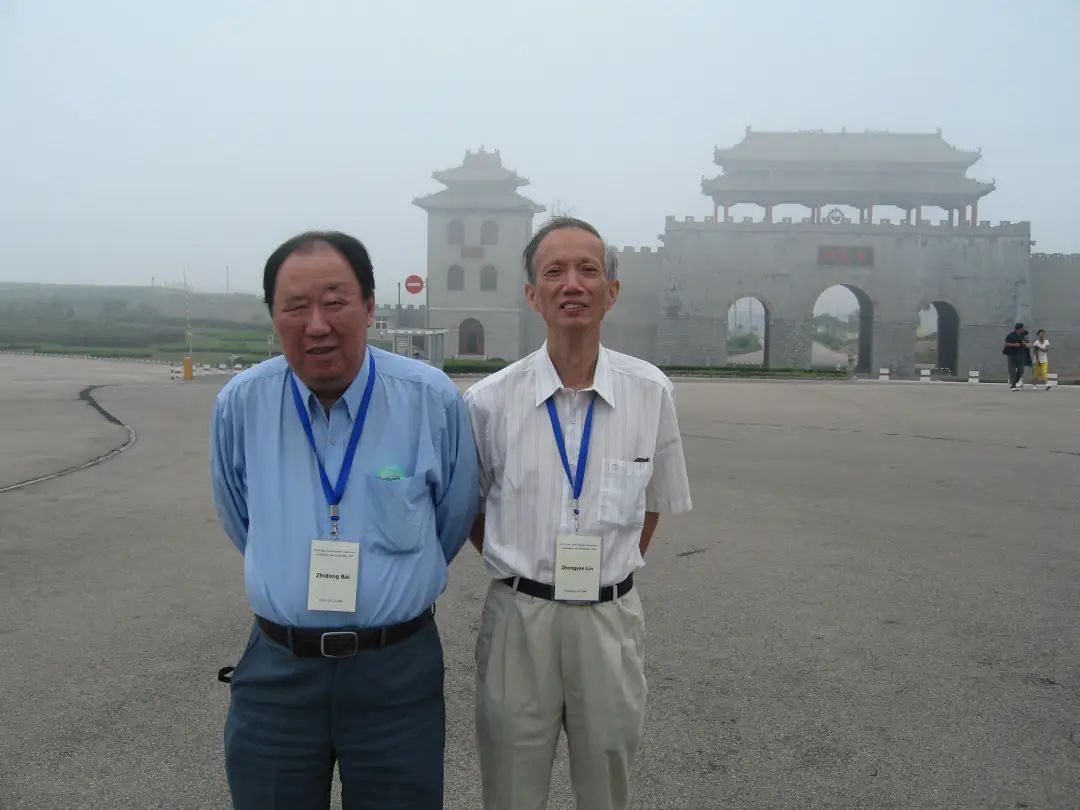
2009年白老师与林正炎老师于威海的合影

白老师和夫人与“大维随机矩阵与高维统计会议”参会人员合影, 2023年11月26日,恰逢白老师80岁生日。
注:访谈内容经过白志东老师审阅